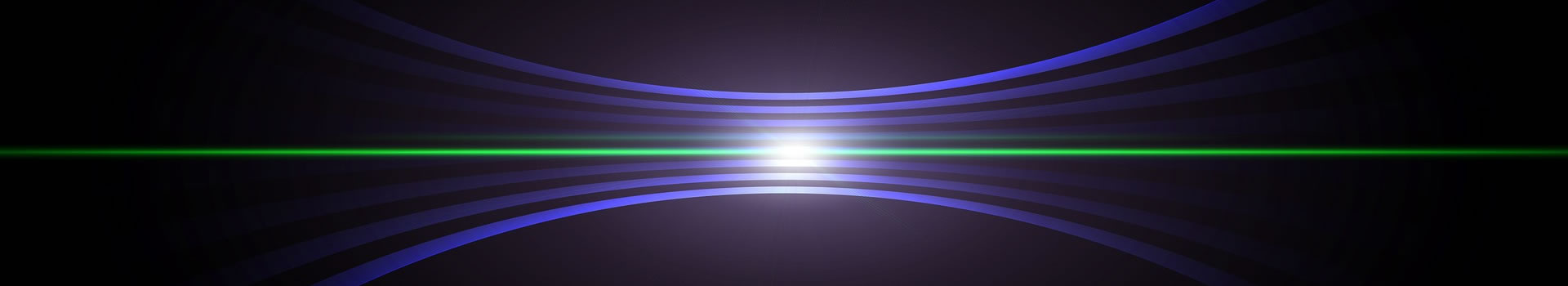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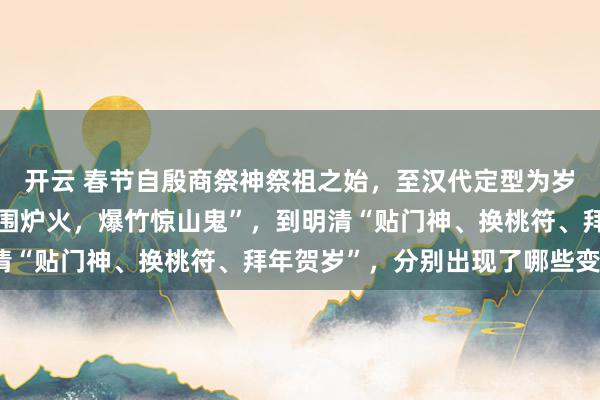
殷商那会儿,年头岁尾最大的事是“祭”。祭谁?祭神,祭祖。为什么祭?说白了,是怕。人对未知的力量怕到骨头里——严冬、灾祸、死亡。所以要用最隆重的方式,献上最好的牺牲,祈求庇佑。这不是节,是生存仪式。它的核心是“集体”,是部落、宗族在自然威力前的颤栗与团结。它影响的是族群认同:我们是一个巫祝之旗下,共同求存的群体。
到了汉代,“春节”才真正定型为岁首元旦。汉武帝颁行《太初历》,正月初一为岁首,这事儿意义太大了。它意味着“年”从一种模糊的时令恐惧,被国家权力装进了精确的历法框架里。从此,“过年”有了官方指定的日子,一种由国家背书的秩序感诞生了。人们开始“拜年”,不仅是祭祖,更是官吏之间、君臣之间的礼序演练。影响是什么?是“国家时间”开始渗入“民间时间”,过年不仅是求生,也开始有了政治与社会的序位意味。对普通人来说,它开始成为一个可以期盼的、规律性的生活节点。
唐宋是春节气质大变的关键。你读唐诗宋词,里头过年气息浓得化不开。“守岁围炉火”,这句太有画面感了。祭的意味还在,但“家”的核心地位空前突出。一家人围炉而坐,通宵不睡,等待新年。这温暖抵抗漫漫长夜的形式,把过年的重心,从室外的、集体的祭祀,拉回到了室内的、家庭的团聚。这是精神内核的一大转折:从“向外祈求神佑”,转向“向内凝聚亲情”。
展开剩余71%再看“爆竹惊山鬼”。火药在这时普及了,竹子换成了纸筒,响声震天。它还是为了驱邪,但多了太多热闹的、甚至娱乐的色彩。唐代长安、宋代汴梁,那简直是全民狂欢。官方搞“傩戏”,民间逛“关扑”(类似庙会购物抽奖),吃食也精致起来,“五辛盘”、屠苏酒。影响深远极了:春节的“欢庆”属性,第一次压倒了“祭祀”属性。它从庄严肃穆的仪式,变成了可以享受的佳节。市民阶层兴起,商业繁荣,让过年多了太多物质与娱乐的快乐。它塑造了中国人“团圆即喜庆”的深层文化心理。
到了明清,春节的模样就非常“现代”了。你看《红楼梦》里过年,仪式繁琐得像一部百科全书。“贴门神、换桃符”,这已是家家户户的规定动作。门神从神荼郁垒变成秦叔宝尉迟恭,桃符演变为春联,祈福的文字越来越个性化、文学化。这意味着,春节的仪式从“请神”,开云官方体育app官网越来越像“装饰生活”与“表达愿望”。
“拜年贺岁”在明清也成了社会网络的大编织。官场有“团拜”,民间要走动遍所有亲朋。送“拜年帖”(最早的贺年卡)都成了产业。这影响是什么?春节成了年度社会关系的总检阅与再确认。它是一个巨大的社交引擎,维持着宗族、乡邻、同僚之间复杂的人情网络。同时,过年期间的集市、庙会、百戏杂耍,达到鼎盛,经济活力全被这个节令调动起来。它成了一个集信仰、家庭、社交、经济于一体的超级文化综合体。
捋下来,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:
精神内核上,从“惧”(祭神避灾)到“敬”(祭祖循礼),再到“亲”(家庭团聚),最后到“乐”(欢庆游艺)与“和”(社会和谐)。恐惧逐渐淡化,现世的情感和乐趣成了主角。
社会重心上,从“集体”(氏族部落)到“国家”(统一历法),再到“家庭”(唐宋围炉),最后到“社会网络”(明清拜年)。个人的归属感,在一层层的关系圈里被确认和温暖。
形式内容上,从“单一祭祀”到“综合庆典”。吃穿用度、诗词书画、娱乐游戏,所有生活与文化的精华,都往这个节里装,让它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总容器。
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它定了我们生活的节奏:再难,过年也要回家,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时间归属。它塑造了我们的情感结构:团圆、祈福、迎新,这些基本诉求,年复一年在强化。它也成了文化的保险箱:多少传统技艺、饮食、民俗,靠着一年一度的“展演”才活了下来。
更深的,它给了一个农耕文明的后裔们,一种面对时间循环的独特智慧。你看,我们不过“新年快乐”,我们说“过年好”。“过”这个字多妙,是渡劫,也是享受;是告别,也是迎接。把所有的恐惧、艰辛、不如意,都在一套热闹的仪式里“过”掉,然后郑重地翻开新的一页。这是一种多么积极又务实的生存哲学。
所以,春节为什么能穿越三千年?因为它最懂得变通。内核从神坛走向人间,形式从简朴走向丰盛,始终紧扣着中国人最根本的需求:对自然的敬畏,对亲情的眷恋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以及对时间流逝那份深沉又达观的安顿。
最后,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收尾吧,它虽不是直接说春节,却道尽了一切传统传承的真谛:
“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。”
我们过年的种种仪式与情感,就是“各美其美”;我们分享的年味与祝福,便是“美人之美”;而这千年节俗在流动中汇聚成的壮阔长卷,不正是文化上“美美与共”的最好写照么?这“和而不同”的温热,大概就是春节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了。
发布于:贵州省
